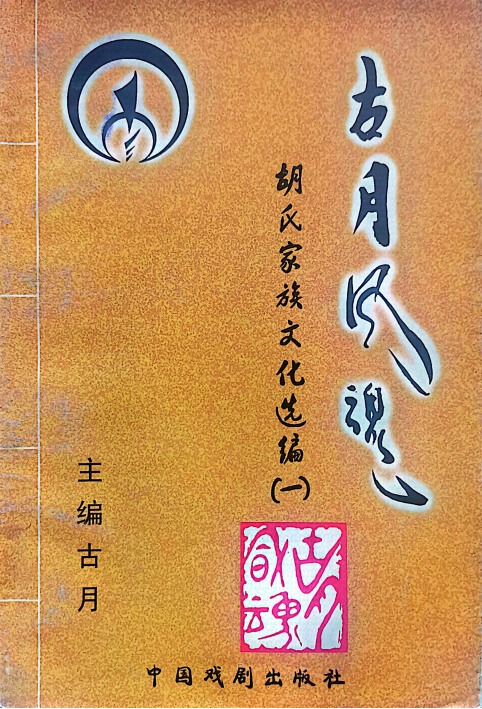陈亦民: 再读《裂变》有感
发布时间:2024-11-22
作者:胡大同
点击量:0
再读《裂变》有感
陈亦民
十多年前,读过胡砚先生以“土改 ”为题材的长 篇小说《裂变》,很有所感,当时吟成一首《七律 • 读胡砚先生<裂变>感怀》 :
卷展沧桑裂变时,风狂雨暴嫩江支。
童年烙印传神画,晚岁升华著史诗。
乍暖还寒生百感,行邪害正费三思。
胡公润色丁周笔,砚注真情果满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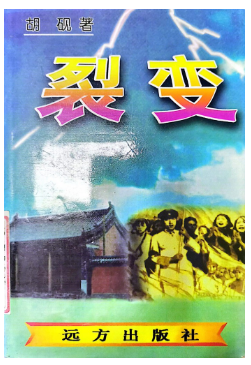
《裂 变》(点此可阅读原著)
前几天,胡砚先生的女儿胡咏梅女士告诉我,《裂变》早在 2006 年就曾再版,她父亲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很是高兴。我向胡砚老师表示祝贺。《裂变》这部长篇的价值和成功,方家扎拉嘎胡先生已在《处女地上的一朵新花》这篇序言中,阐述得全面而又深刻,我佩服而又崇敬。
我这里想说的是再读《裂变》产生的新的感想。我出生在日寇投降后的第150 天。我记事时,辽西农村的“土改 ”已经搞过,我家划为贫农,分得了耕地和房子。父亲是乡村医生,工作队长动员父亲参军,那时父亲已39 岁,有了四岁的哥哥和不到两岁的我,舍不得离开。家里献出8大地窖准备盖房的粮食作军粮。第二年锦州战役打响,父亲参加担架队,七天七夜没驻脚。回家时,已经看到屯子,却再也迈不动步,倒在路旁起不来,是乡亲们看见了,抬回家中。在炕上躺了一个月才下地走动。
从我记事起,当地人都把“土改 ”称作“大风暴 ”,总说“大风暴 ”那年如何如何。说起斗地主分田地,人们的神情总有些不同寻常。土改工作队长、区长手里都有枪,他们都有杀人的权力。
上学后,课本里学到《半夜鸡叫》,小人书里看 到《白毛女》,电影里看到《红色娘子军》,忆苦思 甜时看到《收租院》,对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这些地主恶霸,当然是满腔仇恨。甚至看到扮演黄世仁、南霸天的演员陈强,都要吐一口吐沫。打倒地主,是应该的,天经地义。
我爱读小说。上初中的时候,我读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同人们谈论的“大风暴 ”并不完全一致。读到胡砚先生的《裂变》,觉得更接近东北地区当年土改的真实。胡砚先生以刚刚记事的年龄,经历了那场大变革。童稚的观察,留下永不消失的烙印;成长中的的探索,留下难以磨灭的足迹;老成的思考,留下证明历史的记忆。这些烙印、足迹、记忆,是很宝贵的。这些,是一个人的人生,也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自神农尝百草、教稼穑,中国就是一个农耕大国。土地就是国民的饭碗。但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数千年来,绝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占有,他们借此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无地和 少地的贫下中农,却终年辛勤劳作,不得温饱。“耕者有其田 ”是中国农民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
数千年来,神州大地上群雄逐鹿、改朝换代,无不围绕着争夺土地而展开。历次农民起义,也无不因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而发生。 农民起义也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土地所有权。但是,总体上这种改变,只是南霸天变成了北霸天,李家王朝变成了赵家王朝。明朝李自成起义,曾提出“均田免粮 ”的口号;清朝太平天国起义,也许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等到坐上皇帝宝座,还是把天下土地当作自家所有,分封给子孙后代,皇亲国戚,而那些曾经脑袋提在裤腰带上跟他们造反的农民,还是只能给地主纳粮交租。
历史上,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国人就会拥戴他,听他的话,跟着他走。土地问题解决好了,国家就安定,社会就进步。
2300 年前的孟轲,提出“ 民为贵,君为轻 ”,使“ 民有恒产 ”,被后人称为“亚圣 ”。西汉晁错,“重本抑末 ”削夺诸侯封地;北宋王安石推行变法“抑制豪强 ”。他们都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
1924 年,孙中山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明确提 出了“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 ”的主张。至今被 称为“ 国父 ”、“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
中国共产党从 100 年前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镰刀锤头 ”标识在旗帜上,把“耕者有其田 ”作为奋斗的最主要任务之一。领导农民运动也是毛泽东革命之初最主要的担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二篇著作。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 ”,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贫苦农民才跟定了共产党。人民军队在“ 白色恐怖 ” 中从无到有,建立起多处革命根据地。即使在面临“第 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生死关头,还有人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日本鬼子对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是从五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陕北民歌才唱出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
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只有127 万人,到全国大陆解放,三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军增加到550 万人。林彪出关进东北时,与他一起出关的只有11 万多人,辽沈战役胜利后挥师入关,“四野 ”已有 100 多万人。 三年多时间里,在东北战场上,大的战役就有过四战四平、四保临江、辽沈战役。把这些战役中的减员计算在内,“ 四野 ”人数增长了 10 倍多。这些人是从哪 里来的?经查资料,除了先期进入东北的、从冀热辽 军区划入的、从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从日本军人投诚的,还有70 多万人,这些人都来自于解放区的翻身农民!
我1962 年初中毕业来到突泉县和平屯,这是个蒙 古族居民占八成以上的自然屯,土改时还不到 50 户人 家,竟有 21 人参军,其中有给乌兰夫开车的、当警卫员的,有曾是骑兵第一师战士的。
长江以北广大农村的土地改革,大体上都是伴随着解放战争同时展开的。“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 民得解放 ”,那里就要斗地主分田地,哪里就要保卫胜利果实,参军,支前。解放军就有了充分的兵源和 稳定的后方供给。
一场“淮海战役 ”,蒋家军参战 80 万人,解放军参战 60 万人,而取得完胜的是解放军。据有关统计, 在这场战役中,支援解放军前线作战的民工竟达到 543 万人,其中有担架 20 万副,大车小车 88 万辆,牲畜 76 万头,挑子 30 万副,筹运粮食 96000 万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痛定思痛,也实行了土地改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变革,也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和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土地改革成为台湾民营产业发 展的契机和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对后来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 ”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革的是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命,有数以亿计的人参与,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这场运动又正处于人民革命的力量同反动势力大决战的紧要关头。这条路究竟该怎么走,是需要开创和探索的。从全国来看,东北地区是最早开展土改的;从东北来看,《裂变》故事发生的韩家窑儿,正是绰尔河汇入嫩江之处,处于黑龙江省与内蒙古的交界地。这里同相邻的突泉县,同《暴风骤雨》 中的元茂屯,就是当年土改的发轫之地。正是从这里开始,土改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脚步,走向整个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继而走向华北、走向全中国。这里的土改,为全东北、全中国土改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样板, 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道路肯定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 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步伐就是在不断地选择和矫正中前进的。这里的实践为《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土地改革法》提供了脚本。
《裂变》的故事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蒙太奇式的笔触,塑造出关老叔、关杰、关山、信正、老 校长、莲花、阿图、金光、朱昔等众多活生生富有传奇性的人物,情节惊心动魄而又真实可信。故事的演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家乡的山川风貌,当地的方言俚曲,就像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边。那些富有典型性格的人,就像你交往过的这一个或那一个。 而这些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所反映的,又是普遍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
社会无论如何发展进化,人类是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的。土地所有权是人类社会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土地所有制关系到农民的穷富、农村的兴衰、农业的进退。我不大懂政治经济学,我当过农民, 对农村有亲身体验。
1964 年,我在生产队当会计。亩产达到 160 多斤, 年终分红,每个劳动日值 1.26 元,社员们都很高兴, 说好几年都没有这样的收成了。我说,“农业发展纲要 ”规定,亩产要达到 400 斤,咱们还差得远呢。有的社员就说了,那也不是做不到,咱们这里一垧地打过十多石苞米!我很惊讶!一斗苞米 55 斤,一石就是 550 斤,十石就是 5500 斤。一垧地 15 亩,亩产就是 360 多斤!我不敢相信。社员说,单干时常有这个产量。我说,那现在为啥达不到?“入了高级社,地头往回缩。 ”这是一个不识字的社员说的。简单的十个字,说明了一个大道理。社员们说的不是假话。“包干到户 ”以后,多年不能实现的“农业发展纲要 ”规定的指标,几乎是家 家都达到了。
1984 年,我在巨力中学当校长时,学农基地种的苞米,亩产预算超过了一吨。盟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来地头留影。我在突泉县和平屯居住了 21 年。初到和平屯时, 这个屯分成两个生产队,共有 60 几户。其中有 4 户地主,是王全、王顺兄弟两家和吴白虎、吴老虎兄弟两 家。王家祖籍在山东,是汉族人。闯关东到前郭尔罗斯,有了积蓄,来到突泉六户,做起了小买卖。有了 钱又到柜山扎拉嘎沟里,买了几十垧地,盖起窑。所以这里叫王全屯。几代人都同蒙古人做亲,就变成了蒙古族。我到和平屯时,王全有 60 多岁,大儿子王英在部队是团级军官。三儿子王化成、四儿子王来英、五儿子王春英都是社员。吴家原籍在辽宁朝阳,为躲 避 1891 年那场暴乱,举家逃难,几经辗转,来到柜山扎拉嘎,在西沟买了地,在封山脚下盖了窑。伪满时 移民并村,进了王全屯。我到和平屯时,吴白虎 70 多 岁,儿子吴兴德是木匠。当初,我是把王全、吴白虎 和他们的子女,当作黄世仁、周扒皮看的,后来我觉 得不准确。那个时候讲成分,生产队的队长、组长、打头的、贫协组长、技术员、会计、现金员、保管员、 记工员、饲养员,都没有地主富农的份。有些技术含量高的活儿,却常常被成分高的人包了。王化成干庄稼活真是一把好手,快捷、利索。割谷子“单抱趟 ”, 二三十号人同时开镰,他总是最先割到地头。他割过 的地垄,不漏掉一棵谷子,捆得结实,摆放整齐。留下的茬子不超过二寸,而且一般齐。王顺的大儿子王化福的手艺是盘灶搭炕,他盘的灶不倒烟,搭的炕热 得全。他给生产队放牛,从山上割来黄榆树条子,编成土篮子,背到六户集上换回日用品。生产队造车修 犁,各家盖房搭屋,修门窗家具,就要找吴兴德。我 注意到其他生产队,也都有这种情况。几年前看电视连续剧《闯关东》,我忽然想到, 王全、吴白虎同剧中人朱开山应该是一路人。在土改 时,朱开山会划什么成分呢?
最近,在“百度百科 ”上,有人把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作是又一次土地改革。正是“包 干到户 ”拉开了全国“改革开放 ”的序幕,我国的经 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才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裂变》的可贵之处,不但讴歌了嫩江流域这场 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讴歌了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的兄弟民族之间的深情厚谊;还站在历史的高度,颂扬了正确对错误、正义对邪恶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 这一点,意义更加广泛而深远。
一场奔腾而来的革命潮流,总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真正的革命者也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修正错误。更难免有些心怀鬼胎之人, 或是逃避成为革命对象,或是要借革命的力量实现个人的野心,他们总是以“左 ”的面孔出现,把自己装扮得更革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往往会受到赏识,得逞于一时。这样的人一旦有了权势,就会喊着 更蛊惑人心的口号,做出对革命事业、对人民群众造 成更大的损失的事来。《裂变》中的金光、石女、程信,正是这样一些可恨、可憎、可怜之人。不管人们如何唾弃,社会如何进步,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土 改 ”中有,“反右 ”中有“文革 ”中有,“改开 ” 中也有。他们总会在新的历史进程中,花样翻新,绵延不绝。《裂变》把时间跨度拉得很长,让这些败类反复出现,有很现实的警示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些国有企业一夜之间破产了,而有一些人一夜之间暴富了。这些人不敢把侵吞的财富留在国内,而是存入国外的银行,或是当“裸官 ”,或是“跑路 ”。他们同卖国的汉奸没什么两样, 是当下的老百姓最痛恨的。每每揪出一个、一串、一窝腐败分子,人们都拍手称快。但是“老虎 ”是打不尽的,“苍蝇 ”更是拍不绝的。我们对敢于吃人的老虎,要有制得服它的利器和关得住它的笼子。对于数量庞大的“苍蝇 ”,要准备好拍子,有封闭好的居室,不要让它污染我们的饮食、空气和阳光。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振兴,前进的路上还有很多敌人。外部的敌人很强大,但是最危险的敌人还在我们内部。对外、对内,我们都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搞文学艺术的都是文人。文人都会读过很多书, 包括古今中外导师、领袖、圣哲的经典。这样,文人 就多了观察事物的眼睛。所以在社会上,文人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信任。文人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品当然要歌颂我们蓬勃向上的事业,歌颂我们的英雄豪杰,要有主旋律,正能量。主是同次相比较而存在的,正是同邪相斗争而生成的。人世间有众生相,有烟火气,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乌托邦。真实地反映历史,真实地表现社会,真实地塑造人物,是作 家、文人的良知。胡砚先生是我们地区为数不多的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之一,他用大作《裂变》给我们做出 了榜样。
2020 年 12 月31 日
上一篇:
陈亦民诗词:七律 • 无题下一篇:
陈亦民诗词:参观扎赉特旗农耕博物馆